ChongMingS.COM崇明網訊 醫生們為患者想到了更遠的一層。他們普遍擔心,全國集采是帶量采購,中選支架每年按集采規定的量賣完之后,就不提供了。也就是說,每到年底,患者可能就用不上這些便宜的支架,只能選未中標的那些。

2020年11月中旬,上海一家三級醫院的心內科冠脈支架手術量驟降90%。除了需要馬上做手術的急性心?;颊撸蟛糠只颊咭筢t生將手術日期調整到2021年1月1日之后。
他們像參與一場期待已久商品的打折促銷。1月1日之后,占心臟支架手術中90%費用的冠脈支架,這些支撐他們生命的必需品,由均價1萬多元,降低到幾百元,相當于降到1折以下——已不再是奢侈品。
同樣的變化,也出現在距離上海兩小時車程的江蘇南京和東北齊齊哈爾的兩家三甲醫院的心內科,不出意外,全國其它地區的公立醫院心內科也是同樣的場景。
改變這一切的是11月7日,國家冠狀支架帶量采購競標現場:冠狀支架由均價1萬多元下降至700多元。這是冠脈支架產品從九十年代初進入中國后的最低價。
“不會再有更低的價格了,你錯過了冠狀支架的黃金時代?!蹦且惶?,東北某省一位三甲醫院的心內科年輕醫生凌霄,體味著他同科室一位高年資醫生意味深長的話。
他錯過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持續二三十年的冠脈支架萬元時代,曾在醫院里打造出包含醫院、病區主任、助理醫生和患者的特殊但又相對穩定的生態圈。而在短短一個月內,冠脈支架沒有緩沖地急劇從萬元時代闖入百元時代,不同的價值觀發生巨大的碰撞,生態圈中每一個角色都受到沖擊,他們如何在調整中保持新的平衡?
冠脈支架的黃金時代,也是支架濫用的時代
凌霄同科室前輩說的“冠脈支架的黃金時代”,始于學術界理論權威對冠脈支架的鼓吹——醫生們給這幾位理論界權威起名“支架王”。
在支架王們的理論中,給冠心病、心絞痛等患者安裝“冠脈支架”仿佛成了靈丹妙藥。加上冠脈支架廠商們的加持,這種理論成為多年來“支架濫用”放在臺面上的理由。
“這些年支架確實有過度使用現象。一般做得比較標準的大醫院不會,就害怕下面剛有做這個手術能力的醫院,會濫用支架?!鄙虾D橙揍t院心內科醫生證實了這一現狀。
但即使一些比較規范的三甲醫院,即便嚴格按照相關標準,只要患者的“血管狹窄達到75%”就安裝支架(而不管這些血管是否是引起患者疼痛的主因,或患者的體內是否有三個甚至以上支架),也造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支架濫用。
因為,有另一種觀點強調,如果患者體內的支架多于三個,就應該到胸外科做開胸手術,不該再裝支架了。一些醫生甚至認為,過去多年來,心內科過度利用冠脈支架,簡直是在和胸外科搶病人。
不同理論博弈的背后,哪種觀點在臨床上會更占上風,背后往往是因為利益的驅動。
在南京的三甲醫院,做介入的心內科醫生收入差別很大。介入醫生分為冠脈、電生理和先心病組,其中,冠脈組的醫生收入最高,但同組不同級別的醫生收入差距依然很大:“有的月收入可能幾萬甚至十幾萬,有的可能就幾千。”一位南京三甲醫院的心內科醫生談到。
高收入的醫生很大程度來自“飛刀”,或者說“走穴”。下級醫院經常請這些醫生去做介入手術,給比較高的傭金。在這位醫生看來,醫院為什么能給出這些錢,背后的原因顯而易見:“肯定從廠家那里能拿到利潤?!?/div>
如果不“走穴”,他所在的南京三甲醫院,副高級別醫生月收入大約兩三萬。
但最近五年,凌霄感覺到醫生們對放冠狀支架的沖動已有減少,他身邊的一些資深醫生,開始讓年輕醫生們對患者裝支架有更細致的思考。
“有的老師,會具體分析是哪個血管引起病人的癥狀。如果狹窄的血管,不是導致血供不足的‘罪犯血管’,即使狹窄率達到80%,這些醫生們也不建議安裝?!睂@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理論,他更為信服,也從內心更尊重做出這種判斷(少安裝支架)的醫生們。
著名心臟病專家胡大一,是凌霄眼中比較尊重的學術權威之一。他常年公開呼吁:應該減少心臟支架的濫用。
胡大一曾是中國引進心臟支架的倡導人。這些年,他見到過很多用了七八個、甚至更多支架的患者?!捌鋵嵑苌儆腥诵枰?個以上心臟支架,除非手術過程中導致其他部位損傷,才需要補償性放置?!彼啻喂_解釋。
對患者來說,放入支架并不是心臟問題萬能的解決方案。比如,放入支架的部位,血管再次發生堵塞的概率較大;而且,放入后需要長期服用藥物,而這些藥物可能會有副作用。對有裝支架指征的患者來說,支架可以救命;而對其他患者來說,不用支架,而用其他治療方式,生活質量可能更高。
終于,在冠脈支架手術進入中國十幾年后,在理論上,支架王們的觀點不再占絕對主導,心內科“大佬”開始分化為兩種態度:一派大力鼓勵裝支架,另一派開始反思,呼吁謹慎裝支架。
最近幾年,后者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盡管對臨床的影響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在凌霄這些年輕醫生的心中,至少在盡量給患者多裝支架外,多了一種可能。
在兩種理論博弈中的患者
在過去幾年,患者的經歷,也體現著醫療圈對安裝冠脈支架不同觀點的博弈。
2013年,53歲的王靜(化名)發現,在上樓梯等活動之后,心口會有明顯的疼痛。癥狀持續了一段時間后,她前往所在湖北縣城的人民醫院(二甲)心內科就診,被診斷為勞累性心絞痛。醫生當即要求她住院(當地醫保不報銷門診費用),并做全身檢查。
檢查結果顯示,心電圖、心臟彩超正常,有中度貧血。醫生建議做心臟造影,如果有必要可以立刻安排裝支架。手術可以由市三甲醫院的專家來做,他每周都會來,“本縣的支架手術都是他來做的”。
她聽病房其他人說,在這里,只要做了造影,基本就等于要裝支架了。她還聽見隔壁病房的病友在走廊上呻吟,說剛裝了4個支架,反而比以前更難受了。有朋友在電話里告訴她,自己之前也在這里被建議放5個支架,但自己堅持去著名的民營醫院武漢亞心醫院,只放了2個支架,后來感覺不錯。
出于對手術的恐懼、術后須長期服藥的排斥以及縣人民醫院的不信任,王靜決定去市三甲找專家看看。之前很熱情的醫生,此時態度冰冷,拒絕給她辦出院或轉院手續,理由是“住院還沒到一星期,不能出院”。王靜找了在本地醫療圈的“關系”,才被允許以自費身份出院。
看過她在縣人民醫院的檢查單,市三甲醫院的一位年輕專家很詫異:“你中度貧血,身體狀況很不適合放支架,如果放的話很可能下不了手術臺。”專家建議她先解決貧血問題,“貧血改善后,心臟可能也會好很多”。
貧血治好后,王靜的癥狀果然好了大半,她開始吃治療心臟的藥物。到2020年的今天,她過著正常生活。
便宜的支架質量不會下降,但用量能保證嗎?
六年前,凌霄剛畢業到心內科工作后,發現國產冠脈支架約八九千元,進口支架幾乎都在1萬以上,兩者價格差距并不大。
他發現,醫生們總向患者推薦、實際也用得多的,是國產支架。一開始,他好奇問為什么。幾個年資高的醫生們臉上總是浮現出蒙娜麗莎般的神秘微笑。日子久了,他逐漸明白了微笑背后的含義——國產支架給的回扣多,而進口支架不會給現金回扣。
國產和進口支架背后的機制,導致近幾年全國各大醫院臨床使用的支架,90%是國產——而本次國家冠脈支架的帶量采購,讓臨床常用的大部分支架都中選了。
一位江蘇民營醫院采購科的主任坦言,在民營醫院幾乎不存在醫生拿耗材和藥品回扣的問題。民營醫院作為一個整體自行采購,冠脈支架的采購價格一般比公立醫院低20%以上。而國家的這次“砍價”,遠超單個民營醫院砍價的能力?!斑@次中選的品牌,我們砍價根本不會砍到千元以下。”她說道。
她所在的江蘇,在2019年作為試點省份率先開展冠脈支架的帶量采購。與全國集采的不同是,江蘇將支架分為“一萬元以下”和“一萬元以上”兩組,降價幅度也相對小,平均降幅為51.01%。例如,上海微創的一款支架 “火鳥”(Firebird 2),在江蘇集采中降到3400元,在全國集采中則以590元中標。這款支架本次的意向采購量是所有產品中最大的,占總量的23.1%。
許多患者擔心的是:變得這么便宜的支架,質量還跟以前一樣嗎?心內科醫生們大多不擔心這個問題——國家藥監局宣布會加強冠脈支架生產企業的日常監管,并發文公布了非常詳細的辦法。
醫生們為患者想到了更遠的一層。他們普遍擔心,全國集采是帶量采購,中選支架每年按集采規定的量賣完之后,就不提供了。也就是說,每到年底,患者可能就用不上這些便宜的支架,只能選未中標的那些。
只夠支撐半年的醫院流水和痛苦的醫院院長
前文提到過的南京醫生說,在他所在知名三甲醫院的薪酬體系中,多數醫生從支架手術中拿到的收入并不多。
“在我們醫院,一個病人做一次介入手術,醫保和自費總花費幾萬塊錢,醫院拿大頭,提到科室的利潤可能就幾千塊錢,而且是一個團隊分。不管裝幾個支架,都是這樣?!彼榻B。
冠脈支架的國家帶量采購,固然對醫生的收入有影響,但影響最大的還是醫院。
整個11月份,文章開頭出現的那家上海三級醫院的院長的不安感一直在增加。那些因為支架降價從2021年元旦開始,決定等到那時才做手術的90%的患者,會將他的不安一直延續下去。
看似冠脈支架手術,在元旦之后會有井噴。但在這位院長看來,心臟病的發病率是固定的,支架手術量并不會因為降價而暴增。
懸在他頭上的,更多是不確定性的未來。
心內科一直是醫院重點學科。全院30多個學科里,心內科的手術量最多,占到百分之八左右。支架手術的收入是心內科的大頭,占到科室收入的一半。
雖然國產支架完全可以代替進口支架,但耗材和藥品的不同之處在于,病人一根血管的細微差異,會影響到植入支架的品規。集采制度之下,中標的支架品類、范圍有限,醫生的手術限制由此增多。勢必會導致一些比較高端的耗材,慢慢從醫院里消失。令這位院長最憂心的結果是——整個科室的手術難度、開展范圍下降——而他一直想帶領醫院開展更多疑難雜癥手術。
這勢必會倒逼院長們在更大范圍上對醫院收入進行規劃和調整。
讓醫院院長們更為頭疼的,是眼下的當務之急——未來六個月的醫院流水。這些醫生們不會考慮的問題,卻讓管理者頭疼。這位上海三級醫院院長算了一筆賬,醫院一年消耗的支架量是1500個,原先平均一個支架是1.5萬,一年要收2250萬。如今,集采任務量是在去年基礎上再增加10%,也就是1650個支架,按照集采700元的價格計算,一年收入只有115萬。
在過去,院長們是依靠流動資金來運轉一家醫院的。如今,醫院流水少了,但相應的手術服務價格尚未調整,醫院的周轉資金縮水?!叭绻中g價格沒有調整,我們的流動資金,只夠支撐半年?!鄙鲜鲈洪L提到,這種情況幾乎在公立醫院都常見,“每個醫院都是這樣,很少有醫院的流動資金能維持醫院運轉超過半年以上,最多維持三個月時間。”
南京的一家三級醫院,同樣面臨流水困境。在去年12個億的收入里,藥品和耗材收入占到一半,其中耗材占到20%。“一家企業的運行,都是靠流水撐著,成本、支出其實是相對固定的。”這家醫院采購科負責人告訴八點健聞,一旦耗材收入降低,醫院資金周轉會受影響。
更深層次的壓力,來自付款期限。在過去,醫院采購耗材,先由供貨商墊付資金,往往是3個月,乃至6個月之后,醫院才償還拖欠款。拉長付款期,在上述采購科負責人看來,資金壓力比較小。“這幾個月里,可以把這些資金投入其他方面,我的經營成本是降低的?!?/div>
2019年,江蘇省醫保局印發《省公立醫療機構部分高值醫用耗材組團聯盟集中采購方案》明確規定,公立醫療機構作為貨款結算第一責任人,應按合同約定與生產企業結算貨款,時間不得超過30天。
“6個月以后掏錢,跟現在掏錢,對整個醫院運營,影響非常大。”
這種畸形但又在過去很長時間都達到奇妙平衡的狀態,隨著國家帶量采購一次次猛烈的調整,會在短期讓相關各方承擔一下子釋放的巨大壓力。
年輕醫生們眼中的“食物鏈頂端”
凌霄和他的同事一樣,沒有料到由國家醫保局主導的這場冠脈支架國家帶量采購,會一下子擠干價格里幾乎所有的水分。
擠掉的水分,在他所在醫院的大心內科室一個月幾百臺冠脈支架安裝手術中,是動輒百萬的巨額數字;這個巨額數字中的一部分,經過科室里少數幾個主導心臟支架手術的病區主任——凌霄和同事們稱他們為“大boss”——的分配,到他這種畢業不久、經驗只夠做冠脈支架手術助手的年輕醫生每個月的收入上,只有小幾千塊。
這幾千塊,比起“大Boss”每個月數萬元的損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他所在醫院的大心內科接近一百名的醫生中,雖然做介入手術的醫生平均收入最高,但最巨額的收入集中在幾個病區主任的手中。
他們平時的收入約在4、5萬之上,如果去外面醫院“走穴”,很可能一個月收入能達到10萬。而他們對應的工資單上的“陽光收入”,最高級別也不過7、8千元,加上科室獎金,約有2-3萬,只有冠脈支架帶量采購前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但這些可以獨立執導難度最大的手術的病區主任們,也曾經歷過凌霄所處的階段:醫學院碩士或博士畢業后,分配到心內科。從級別最低、基本工資只有2000-3000元的住院醫生做起,一步步參與冠脈支架支架手術,從助手到可以獨立手術并指導其它助手手術,最終做病區主任,一般需要十幾年的時間。
凌霄自問,為什么像他一樣的年輕醫生薪水不高,卻要苦苦加班、學習,盡可能多的給大boss做一助二助,參與手術,不斷地往上走?大家有些心照不宣:有朝一日也希望到達食物鏈頂端,在技術和經濟地位上,“大boss”的位置就是他們的努力方向。
在工作的六年時間里,凌霄的內心經歷幾種力量的牽扯:有救死扶傷的職業尊嚴感;有了解了耗材的灰色收入后,看到一些醫生不分青紅皂白給患者裝支架的鄙視;有時也羨慕那些收入高的醫生,對自己的收入和付出覺得不值時的抱怨……
他覺得自己不是最努力的醫生,有時也不太情愿去日夜顛倒地做手術,只是介入醫生大多是男性,總要承擔養家、買房的傳統壓力。他很佩服自己的另一個同事,是一個未婚的年輕女醫生,醫學碩士畢業后主動申請做心臟介入手術,冒著影響生育能力的危險,去“吃線”——這是做介入手術醫生間的玩笑話,因為做手術的過程中醫生要受射線照射,需要穿鉛衣防護。
冠脈支架帶量采購后,每月收入少幾千元,不會對凌霄現在的生活有根本性的影響。只是他曾經的奮斗目標,那“食物鏈頂端”的位置,忽然喪失了吸引力,留給他的是對未來的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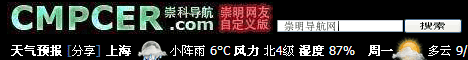
網友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