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MingS.COM崇明網訊 《電子商務法》自1月1日正式實施,要求包括微商、代購在內的電商從業群體補辦營業執照、規范從業,這也提高了這一群體的從業門檻。勞動報記者發現,隨著電商法落地,許多微商和代購已經關閉朋友圈,平臺型就業成為他們的轉型首選。
轉型一
涌向跨境平臺當買手
據《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顯示,電商的直接從業人員和間接帶動就業多達4250萬人,這意味著,中國每18個就業人員中,就有一個人正在從事與電商相關的行業。
lulu就是其中之一。lulu的老公于2010年到美國讀書,兩年之后她以陪讀的身份也去往美國,因此不能在美國工作。家庭主婦的“工作”之余,她走上了代購這條路。
勞動報記者在微信采訪她時,她剛剛掃貨結束,正坐在商場的椅子上稍事休息。而她還在另一邊掛著客戶端,回答客人的問題。她告訴記者,頭一天晚上,她處理一個問題包裹到當地時間凌晨3點。
“于我而言,代購不是兼職或者心血來潮,是個事業。”lulu說道。正是她把代購作為事業的這份決心,讓她早早意識到了做“散戶”代購不是長久之計。
做代購,不僅像淘寶賣家一樣忙,還有著獨特的風險。轉運公司“跑路”是一種風險,如今電商法出臺是政策風險。好在lulu早在一年多前就當機立斷選擇規范化經營。2016年她就在洋碼頭上注冊了店鋪,開始了買手生涯。如今,她的營收翻了幾番,每月光是運費都超過5萬元,在同樣年限的代購里已算是很大體量。而且,現在她已經當起了“老板”,開了公司,開始雇人當買手。
“在美國做代購的風險還是比較高,也聽同行說過有轉運公司跑路,卷走了幾百萬的貨。”現在說起來,lulu還是心有余悸。所以她堅持每一件物品都買保險,并認為“該花的錢還是要花”。據了解,與國內跨境電商平臺合作的買手,采購回來的貨品由洋碼頭官方物流統一發回國內。
“代購路走到盡頭,就轉型去做買手。”她直言,現在很多海淘公司也是招聘代購當買手。她認為這一職業也是一門技藝,“做代購要研究產品、打折趨勢,預估市場,還要研究你的顧客、客戶群,對品牌、流行趨勢也要學習。”
轉型二
做自媒體“拿”品牌授權
小花是上海一位80后的愛美女生,做代購已經超過10年了,最初是自己熱愛購買奢侈品,每次海外購物兼職代購賺路費,客戶圈擴大后,如今她的主要工作是組建“買手”團隊線上服務老客戶。
“代購的品類從護膚品到羽絨服,哪個火做哪個。有囤貨到倉庫,也有直郵到個人。”小花的微信里有幾十個買手群,人數多達近百人,幾乎涵蓋了法國、美國、意大利、日本、韓國等所有海淘熱門國家。她的買手團隊里,有留學生、也有富二代,有全職媽媽、也有上班族。“買手一般會去免稅店買,比如韓國就有政策支持,免稅店價格差不多全球最低,這幾年俄羅斯、迪拜也效仿,專業買手有黑卡、積分、返點返券等等,其實代購就是賺一些差價。”
大約是在2013年,小花的代購業務進入正軌后,她就在上海注冊了一家公司。小花認為,電商法對代購群體不一定利空。“可以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畢竟代購商品即便加上稅也比專柜便宜。”她始終認為,“代購這個行業只會越來越規范,轉向正規是好事,該辦證就辦證,該納稅就納稅。”
小花發現,不久前,身邊的一些代購同行開始轉型做自媒體。“我自己也在寫公眾號,有固定的粉絲,可以定期開團。”她告訴記者,現在越來越多的品牌可以拿授權了,自己更傾向于授權品牌,與國內代理拿貨,一般貿易帶中文標簽,安全有保障。“作品牌代理就必須要開公司,對于有一定客戶積累的個人代購,只要有合法合規的程序,品牌商其實是愿意與之合作的。”“平臺型就業”是大勢所趨
按照統計數據,2017年中國電商交易額達29.16萬億,網售規模冠全球。更重要的是,電商帶動了4250萬人員就業,而全國就業人數為77640萬人,這就表示,中國每18個就業人員中,就有一個人正在從事與電子商務相關的行業。
其中,個人代購、小網店主、微商等群體的就業將直接受到影響。勞動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部分群體此前有許多是辭職后全職從業,而電商法實施后,為規避法律風險,他們最終會選擇兩條路:一是提高成本注冊公司依法納稅;而第二條路就是依附企業級“海代”,轉向“平臺型就業”。
實際上,目前小紅書、洋碼頭等企業級“海代”就實行的是簽約買手戰略,這些平臺上已有上萬名買手。而隨著政策趨于正規化,在過去幾年里,包括洋碼頭等平臺對于原有的買手入駐規則也進行了多次調整與完善,通過提高入駐的門檻,來進一步地提升源頭買手的素養和完善行業制度。
洋碼頭相關負責人表示,其間就包括了不定期核查海外買手信用情況及加強買手準入機制審核環節的監管。除了買手本身之外,對于買手所提供的貨源,渠道等,平臺也會進行嚴格審核。在銜接當地國家法律監管的大背景下,洋碼頭必須要以更細致全面的監管體系來核實每一個買手的資質,包括對買手的信用予以證明,經營資質的驗證審批及借助海外機構核實買手資質,為保障100%的海外正品服務而構筑更全面的買手監控體系。
事實上,電商法正式實施后,各種新型靈活就業開始浮現,電商“平臺型就業”成為了最火爆的模式之一。
于去年8月正式上線的環球買手,就是從代購人群切入,將國外的代購和國內的消費者連接起來。創始人黃凱文將這一商業模式定義為“CBC分享型電商框架”,一個共享的生態架構。
CBC對應的分別為買手、平臺/商家、消費者,由中間的平臺聯合商家,負責商品的展示及價格方案的制定。在平臺規則中,買手不可以自主定價及上架商品,以避免價格混亂的狀況。簡言之,買手主要負責貨源及服務,平臺聯合商家負責商品的上架及定價,共同服務于消費者。
這一模式并不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純電商平臺,更多地是想做一個跨國界的人力資源生態圈。黃凱文舉例說,一個在國外工作的買手,在工作的時候接到了一個訂單。當下她無法去代購,可以在后臺尋找附近的人代發,將人力時間共享起來。各自獨立的代購形成了一個圈子之后,一來可以面對更多元的用戶,二來也可以由平臺和物流公司談判,降低郵寄成本。從業人員權益保護待加強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就業方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新型的就業方式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給予就業者更大的自由權。就業方式的選擇也多種多樣,平臺型就業職業日益多樣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全國總工會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指出,工會組織要進一步加強快遞員、送餐員、卡車司機等靈活就業群體和平臺就業群體的入會和服務工作。這對新時代工會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以上述職業“買手”為例,雖然工作本質類似,但其與“代購”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記者了解到,兩者最大的區別是:代購是散兵游勇,買手則是“正規軍”,而這一“正規軍”背后倚靠的便是“企業級”的跨境電商平臺。需要注意的是,跨境電商平臺對入駐買手有嚴格的審核管理制度,包括其身份認證、海外信用證明等多項材料審核,平時還有不定期回訪更新。
與在淘寶上開店的情況不同,買手往往是以個人的形式在平臺上接單,而大部分平臺也會對買手進行等級管理,從這一模式看,平臺與買手之間的關系界線就顯得模糊不清。
買手的身份困惑,歸根結底,是互聯網+時代下,平臺型從業人員的普遍困惑。滬上勞動法專家周斌指出,在移動互聯高速發展的當下,“互聯網+”企業依托平臺搭建信息的集散地,與從業者簽訂服務協議,由從業者根據需求信息提供消費者服務項目,如在線約車、在線訂餐、在線購物等。此種模式類似于傳統行業中商場與入駐品牌商家之間的合作關系,互聯網平臺等同于商場,為從業者與客戶提供一個交易場所,從中收取一定的服務費,雙方之間并不成立勞動關系。
現階段,這類從業者的權益如何保障?周斌直言,從業者要找準東家,既有利于從業者對自身權益的維護,也便于從業者造成他人權利傷害時的責任分擔。但他同時指出,對于這些勞動者而言,和網絡平臺之間究竟有沒有勞動關系?是否應當簽訂勞動合同并享受相應待遇?發生勞動糾紛和工傷等如何維權?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加快立法速度,并予以有效監管;同時,也需要工會加大對這一群體的覆蓋和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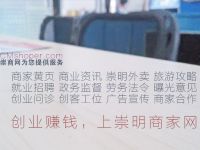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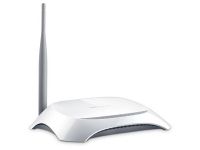












網友回復